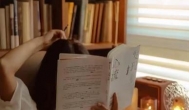年关将至,却总也感受不到年的味道,此时愈加怀念儿时的年了。
我的老家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,二百多户,七八百人口。
进入腊月门,尤其是过了腊八,年味也渐渐浓郁起来。
父母开始忙年,我写寒假作业。
说是忙年,其实也就是父亲劈柴,母亲忙着蒸饽饽豆糕。
大队杀完年猪,我家会分上十多斤肉,母亲会把肉挂在厢房里,这是过年的全部家当。
大年三十,全家人早早起床,母亲会做一锅掺了豇豆的大米干饭,然后做一盆白菜猪肉炖粉条。
父亲领着我们弟兄五个扫院子、挑水、贴对联。

这一切忙活妥当,父亲要郑重其事的请神主回家过年。
父亲神色凝重,上香,点蜡烛,摆供品,然后毕恭毕敬的磕头,哥哥们依次在神主面前磕头作揖,
我躲在炕角,死活不依,母亲见状,劝了父亲:
他还小,祖宗不会怪罪的……
吃过午饭,母亲剁馅。
我会从大柜抽屉里偷父亲藏的小洋鞭,拿出去拆开了放,有水红色,浅绿色的,还有淡黄色。
即使被父亲发现,也不但心会挨揍,因为大年三十,是讲究一团和气的。
吃过年夜饺子,小山村的鞭炮声此起彼伏。
那个年代没有电视,更没有春晚可看,吃过饺子,父亲会催我们早点睡觉,
大年午景要出去拜年的。
我们弟兄几个,像听话的小猫咪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当鞭炮声再次紧锣密鼓的响起,已经是新年钟声敲响了。
我们迅速穿上过年的新衣,揉着惺忪的睡眼,简单吃几口面鱼,浩浩荡荡的出去拜年了。
此事大街上已经人头攒动,拜年的人一波接着一波。
我排行老小,不懂辈分,哥哥喊啥,我跟着喊啥,往往到我这里,屋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。
喊啥不在意,只要给糖就行。
口袋满了,我急匆匆的跑回家,把糖藏在抽屉里,再跟着拜年大军继续前进。
二百多户,几乎跑了个遍。
百密一疏,总有遗漏的,我就一个人再去复查一次,也有问两次的,可是我不知道叫啥。
我就根据年龄推断,年轻的叫哥嫂,中年的叫婶叔,老年的叫爷奶。
为此还闹了笑话,有一次推门进去,开口就喊:嫂子过年好!
不曾想新过门的媳妇羞红了脸:小叔过年好!
有些尴尬,我还是礼貌的收了糖,夺门而出。
大年午景,收糖是第一要务。
然后就是拿着手电筒去捡人家院子里磕芯的鞭炮。
东方露出了鱼肚白,我知道朝思暮想,日夜期盼的年就要过去了,心中陡然产生一丝失落,
心想,下一次过年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......
时光匆匆,如白驹过隙,转眼间我已经人到中年,儿时的年只能尘封在记忆里了。
(投稿人生百态)